(注:又好久没更新博客了,在此贴上几篇近来给一北京旅游杂志《旅行家》写的专栏稿和大家分享)
记不清自己第一次坐火车是什么岁数,只知道是学前,身高未满需要买票的标准,于是和祖母挤在同一张床铺上,被祖母拥抱在怀里,随着车身辗过铁轨发出轰隆隆巨响和摇摇晃晃的韵律中,闻着窗外吹来南洋椰林芭蕉气息的微风,很有安全感地沉沉入睡。这个记忆种下了日后我对火车的特殊情结。
之后,我11岁第一次独自乘坐长途火车,那是我意识到社会险恶但人间冷暖交汇的启蒙课之一。400公里路程,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到最南方的城市新山,当年需要坐十来个小时的火车,车厢里的左右邻舍见我幼小,一个个给我递吃喝的,连连称赞我独立懂事,让我心里好不得意。隔夜一觉醒来后,我发现兜里的钱包被偷走了,扒手却颇有“良心”地在我兜里留了一些零钱,大概是给我打公众电话求救用的(当年手机不普遍)。
而我开始觉得火车一节节的车厢装着一个社会的缩影,是多年后的事。过去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地沿着铁轨满世界乱转,发现自己其实走在历史的轨迹上,一列列的火车是一条政治经济传送带;从马来西亚的殖民痕迹,到中国的铁路红色记忆,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分家而数十载“脱轨”,到欧洲工业革命历史任务完成后而逐渐隐退的火车,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列车的开荒流亡史,今昔往昔在一道道铁轨上交织流转,说不清我的旅程是在往前推进或是倒退。
摊开世界铁路地图,见到一条条黑线像人体的五经六脉般分布在各国,不难察觉这世界上也许有近半的火车路跟帝国主义有着渊源。蒸汽火车的发源地英国,随着工业革命需求伸展其触角到世界各地搜寻原材料,史上最庞大的帝国拉响鸣笛轰隆启动;大英帝国巅峰时期占据了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土地,并在各个殖民地——从西边的加拿大、南边的非洲、至东边的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大兴土木修筑铁路,每条铁轨都是其霸权政治势力的铁证,也是其经济脉搏。即便不是殖民地,如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也是由一名做鸦片、棉花、茶和丝绸等出口贸易的英商,没获得清政府批准下在上海非法建设。
我老家马来西亚的铁路曾是为了运输锡矿石而崛起,轨道将一个个锡矿资源丰富的城镇相连至海港,这一条条的轨道不但改变了马来半岛的地理面貌,也带来了社会人文巨变。19世纪,一艘艘船只将印度劳工运往马来亚修筑铁路,另外,一批批的中国劳工被“卖猪仔”至雨林里开荒淘锡,进而形成了今日马来西亚引以为傲的多元种族社会,但时至今天种族关系依然是一个暗流汹涌的政治社会命题。
我出生时,锡矿产业已近迟暮,再也吐不出锡的矿湖被废置,曾经依赖资源型经济繁盛起来的城镇陷入没落;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每隔一段时间坐火车途经这些城镇,我目睹着夹道的房子一年比一年破旧,先是商店招牌掉落了,接着破瓦穿墙,最后甚至直接夷为平地,而穿过火车窗口见到的人们,都是些留守的老人和小孩。
渐渐地,这条曾是经济输送带的铁轨,物流人流锐减,加上高速公路的大跃进式发展,火车不再是首选出行工具。火车是提速了,服务升级了,装潢和设备也更精致丰富,空调把热带的潮湿高温屏蔽在车厢外,但乘搭长途火车的乘客,只剩下有那些不赶时间,愿意掏比大巴车票更贵的价格,或有轨道情结的人。而火车班次和停驻的站点,也越来越少,有的上百年历史的火车站甚至被关闭,彻底被遗弃了。
但在印度,这个疆土辽阔人口密度极高的国度里,火车依然是当地人赖以移动的工具,也是游客不能错过的经历。不论大小城镇,印度火车站总是拥拥嚷嚷,售票大厅里乘客、乞丐、扒手、游民、小贩、执法者、老鼠蟑螂等川流不息。火车进站时,人潮汹涌,你推我挤,不少当地乘客不用车门,而是直接从窗口连人带行李攀爬进车厢。
印度所有的火车班次都叫“Express”(快车),即便有的时速不到40公里一小时,又或者每到一个小镇村落都停驻片刻,加上误点状况频发,如果你是赶路或急性子的人,印度火车也许会让你很崩溃,但一趟火车之旅将让你窥视印度的万象社会百态。窗外的风景,包括早晨蹲在铁轨上大解的人们,那话儿赤裸裸展示给咆哮而过的列车;车厢内,小贩、卖艺的、乞讨的、偷窃的,夹杂在人群中,当地人建议坐火车时,应该带上粗粗的铁链和锁,牢牢地把行李固定在座位下,以防盗窃。旅游指南书也提醒游客要提防车厢内接受陌生人提供的免费饮食,不是怕你拉肚子,而是怕你给下了迷药,丢失财物。但是,我觉得分享是火车旅程的乐趣之一,只好凭直觉和信任自己的辨识力,无需处处防着陌生人,那样太累了也太乏味了。
印度铁路在英殖民时期开启,目前其铁道公里数排行世界第四(按序为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但运载的人流数量排行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当年英国人在此修筑铁路不仅为了运输原材料或深入管辖庞大的领土,也包括便于自己“避暑度假”,而因此创下了一些铁道工程的技术性突破。比如通往北方山区Shimla城的窄轨火车道,车厢看起来像游乐园里的玩具车,沿着峡谷山脉缓缓盘转而上,当年属于一个工程奇迹,为的是让害怕酷热盛夏的殖民者,在夏天时把行政中心搬往凉快的高山上,类似“夏宫”的概念。今日的Shimla看起来像个英国小镇,主街道上一排排的Tudor式房子,百年老字号餐厅里的服务员像受过英式管家训练般地立得笔直,平日用手抓着吃的印度煎饼,也要优雅地拿着刀叉品尝。
1947年独立前,印度铁路已经相当完善遍布全国,但巴基斯坦的成立,却让原本相连两地的多条铁路,尤其是在两国Punjab省一带,一度血染成河。殖民者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硬生生在印度版图上标明了两国分家后的国际边界线,接着统治者们没有预想到的,史上最短时间内最大型的人类大迁移发生了,穆斯林从印度境内撤离前往巴基斯坦,兴都和锡克教徒从巴基斯坦迁移到印度,这些老百姓们因安全问题,遗弃了世代定居的地盘,不少人连夜乘搭火车逃离,有的却永远到达不了目的地,有的在火车站就已被屠杀,有的在路途中火车被袭击丧命。那场大迁移的死亡人数没有权威数据,估计介于50至100万人之间。两国间的国际火车后被暂停,直到1970年代末再次启动,但只限一个口岸进出,安检漫长森严;硬件沟通设备虽然再度衔接上,然而心理创伤和对立情绪,至今依旧未平复。
同样曾是殖民地的柬埔寨,在法国管辖下只有几百公里的单轨铁路,后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期间的反殖民抗争和内战中被严重破坏,后在苏联资助下修复但火车服务依然稀缺。我于2005年到当地旅游时,Battambang城附近的村落因火车一周才经过一次,当地人就自制“竹子火车”(Bamboo train)利用轨道载客运物。他们拿竹子绑成一个平板,架在两根铁棒上,套上四个小铁轮,再以改装的小型发电机启动这种独特的“露天火车”。因为是单轨铁路,所以如果有另一辆竹子火车迎面而来,那就要看谁的车上人和物较少就得让道,这得把火车卸装至轨道边上,等另一辆车过去了,再次安装后上道。
竹子火车在当地叫做“Nori”,演变自英文的“Lorry”(货车),是当地居民的短途交通工具,近年来也成了游客猎奇的旅游项目。车速其实还不算慢,可达到40公里一小时,我坐在上面紧握着竹子平台,深恐被前进的动力抛出车外,迎面而来的风让我有点睁不开眼睛,头发也被吹得乱七八糟,感觉蛮刺激的。
但是,随着柬埔寨去年宣布将大事开展铁路设施,这种违规交通工具可能会成为历史。自从上个世纪末,亚洲各国就已开始谈论建设“泛亚铁路”,即一条串联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越南至中国的铁轨,那么一来就可以继续衔接至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轨道,一路通往欧洲。这个计划的关键缺口就在于柬埔寨,因为其他国家的铁路系统基本成熟。目前柬埔寨已获得亚洲发展银行和澳大利亚政府出资复建铁路,预期2013年完成,到时候,也许“竹子火车”将不再复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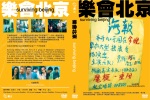
Leave a comment